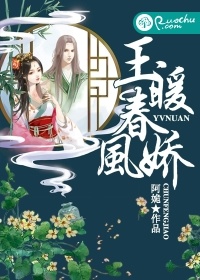三月暖阳的春光之中,一袭鸭卵青斜纹翠竹纹绣长袍的凤缺施施然而来,白玉峨冠,脸沿冷硬而清隽。整个出尘若仙,惹的曲水河两岸姑娘粉面娇羞,端的是好一副美景。
凤酌眼皮一抬。就见凤缺似乎直直朝她而来,他手里拿着束翠色绿叶香兰。约莫是个姑娘,都是想要得那束香兰。
楼逆眼梢看过去,瞧着凤缺目光微微一顿,继而嘴角上翘,他扬了扬手里凤酌起先送予的香兰,挑衅意味十足。
凤缺自然也是看到了楼逆手中的香兰,他步伐微顿,复又恢复如初,谁也没察觉。
“长老,”眼见凤缺近了,凤酌躲避不过,她只得起身,提着裙摆裣衽行礼,“可是有吩咐?”
凤缺摇头,他握着香兰的手一紧,后递给凤酌道。“给你。”
凤酌面有疑惑的接过,抬头见依旧面无表情的凤缺,心里自发的就为他找了借口,约莫长老是没中意的姑娘,故而香兰不好送出,免得平添误会。故而才扔给她。
轻风之中,她髻上的红丝绦随风而动,连着耳铛亦是如此,便是裙裾之间那石榴红底的金合欢,真似摇摆不定。
凤缺深沉地看了凤酌一眼,并不理会楼逆的情绪,他见凤酌将他那束香兰与楼逆送的那束小心地放到一起,心头蓦地就开怀了几分,衣袍划起优雅的弧度又落下之时。旋身离去。
楼逆眼神锐利如刀片地戳在那碍眼的香兰上,抿了抿薄唇,委委屈屈的道,“分明是弟子最先送予小师父,怎的要和凤缺的放一块……”
凤酌抬手屈指就在他额头敲了一记,“要叫长老。”
后又道,“长老也二十有余了,至今未娶亲,想来是一心放在玉雕之上,故而才耽误了,约莫这次上巳节,也是家主逼迫他前来,没中意的姑娘,香兰也不能随意相送,故而才扔给我,也算善后。”
听这言辞,楼逆才不管它真假,总是师父的想法最重要,且见凤酌的模样,并未多先其他,他便暂且放下心来。
却说凤酌得了凤缺得香兰,倒让旁的姑娘家眼热嫉恨起来,可碍着上巳节曲水河边,人多嘴杂,故而多数的姑娘只得暗暗隐忍下,还要端出一副大方得体的笑脸来。
可总有那等拎不清的蠢货,最靠近凤鸾的一姑娘,也不知是哪家的,先听凤鸾似是而非的说了那么些话,这会见又有男子不断给凤酌扔香兰,便十分不忿的讥诮道,“光天化日,也不知点廉耻,竟与族中小厮徒弟坐的那般近,真是好没脸面,叫人钻地缝才好。”
隔的并不远,那姑娘声音不大,可却让周围的人都听的清清楚楚。
凤酌淡淡地瞥了凤鸾一眼,后目光落在嘴碎的姑娘身上,冷笑一声直接骂道,“咬人的狗不叫,乱吠的,岂算家犬乎,怕是畜牲野狗之流,脏眼。”
楼逆本想开口教训的,哪知还未来得急,便听得凤酌这实在恶毒的话,忍不住就想叫好。
“你骂谁?”那姑娘眼眶瞬时就红了,她扬手指着凤酌,气的面色青白。
凤酌一扬下颌,当即翻脸,“矫揉造作,虚伪至极,合着本姑娘的性子好?也不打听打听,我凤三有哪些手段,就敢说三道四,再有半句,我撕烂你的嘴去!”
毫不留情,到世所罕见的地步,实在让听闻的旁人瞠目结舌,有那本想送上香兰的男子,赶紧背了手,走的远远的。
那姑娘更是畏惧的浑身都在发抖,她扭头看了看凤鸾,手脚无措,就差没当场哭出来。
凤鸾讪笑一声,他伸手敛了敛耳鬓细发,和气的道,“三妹妹,怎的这般大的火气,今个是上巳节,又何必与人不快?”
凤酌哪里不晓得凤鸾的花花心思,不就是看凤宓不在了,想挣凤家大姑娘的名头,日后若再嫁与杨家杨至柔,多半就能重振门房。
她不管凤鸾使何手段,但别拿她来当踏脚石做筏子就行。
而眼下,这人是没半点识务,她也不介意让人看得清楚些,于是,她睥睨望过去更为蔑视的道,“谁是你的三妹妹?信口雌黄,有胆没见识的狗屎,信也不信我断你姻缘?”
凤鸾心头一跳,这最后一句话叫她再多的火气都发不出来,只得期期艾艾地看着凤酌,好不可怜。
“凤三姑娘,好大的口气。”一道带沉而冷厉的声音从凤鸾身后响起,众人散开,就见一身宝蓝色圆领斜襟长衫的杨至柔手持香兰地走了出来。
他将手里的香兰递给凤鸾,看着凤酌面无表情。
凤酌琉璃眼瞳微眯,她倒是没想到,这人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愿意为凤鸾出头,不过一转念,她也就明白过来,无非是些情深意重的戏码,虽说是家族利益而联姻,可总要后宅安宁而信任才好方便行事。
故而,杨至柔也不吝啬对凤鸾展现一下英雄救美的手段。
“哼,”楼逆反应更快,他撩袍起身,将凤酌挡在自己身后,狭长凤眼之中冷光溢出,“姑娘家的事,堂堂七尺男儿,也好意思插手,真是丢将男子的气概都丢尽了。”
楼逆反将杨至柔一军,叫周围同样是男子的诸人看他的眼色就变了。
哪知,杨至柔一拂宽大广袖,颇为魏晋明仕风骨的笑道,“楼公子严重了,杨某只是觉得凤三姑娘言语有失偏颇,故而忍不住多嘴了句。”
楼逆勾唇浅笑,然他说出的话却非常不美,“多嘴?杨公子真如长舌妇。”
这话一出,就有围观者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凤酌对这等嘴仗不甚有兴趣,她更喜直接用拳头,遂跟着起身,将徒弟和凤缺送的香兰递给赤碧拿好,其他的一脚踩过去,招呼了声,“徒弟,走了。”
楼逆应声,意味深长地看了杨至柔和凤鸾一眼,继而才追上凤酌离开曲水河岸。
如此好生的一场上巳节,竟被这徒弟两人搅合的不成模样,偏生这两人还毫无所觉,径直回了凤家桃夭阁,凤酌想了想,便去找凤一天,问了最近玉矿山之事,再状若随意地挑了两三个玉矿山,只道去走走,顺便带徒弟见识见识。
凤一天不疑有他,对凤酌主动往玉矿山去的行径,自是赞同不已。
支会了家主,凤酌便让楼逆准备出行之物,旁的她再都不管。
楼逆自然明白,这是要去寻龙脉,按捺下心里的亢奋,急匆匆打定行装的同时,也去岳麓书院,一应事交代给易中辅,并叮嘱他多多注意京城之势,旁的是半点口风都不露。
临到出行那日,一大早,凤酌穿了轻便的窄袖黛色衣裙,与楼逆一人一骑,辞了想要跟随的四位婢女,动作利落的翻身上马,一扬马鞭,就欲疾驰出城门。
哪知这当——
“酌姐儿……”远远的凤宁清竟然追了出来,她身后还跟着两三婢女,不停地喊着她慢点。
凤酌皱眉,她看了眼楼逆,示意他出面。
楼逆笑着调转马头,恰好就在凤宁清靠近之时,拦了她去路,将之于凤酌隔开来,“宁清师父,有何吩咐?”
凤宁清止步,她探头看了看凤酌,奈何楼逆遮挡的严实,她根本看不到,只得仰头对楼逆道,“徒孙,此去路途遥远,当要仔细照顾好酌姐儿,在矿山,寻了玉石,还是赶紧回来的好。”
才两三句话便不离玉石左右,便是楼逆这等深不可测的性子,都怒而发笑,“不劳宁清师父费心。”
瞧着凤宁清还想说什么,楼逆又赶紧开口,“时辰晚了,宁清师父若无事,我与师父不敢耽误。”
说着,对她一点头,楼逆与凤酌直接就打马而去。
待两人都走的来只剩个黑点,凤宁清还久久地回不过神来,其中有名婢女撇嘴道,“宁清师父,三姑娘还当你是恩师么?如若不然怎的都听不明白您的言下之意呢?”
凤宁清苦笑一声,嗫嚅道,“我本就与之断了师徒关系……”
“是这样的没错,”那婢女还不遗余力的挑拨,“可好歹您也将三姑娘养大成人,这都说养恩大过生恩,且还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,这些情谊,哪里是能轻易就抹掉了呢,叫婢子说,您得时常提醒三姑娘,免得她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您徒孙身上去了,到时那等稀有玉石,还有您的么?”
凤宁清咬了咬唇,她有心想呵斥这婢女不尊卑,可只要一想到这人是凤修玉拨到她身边的,便只得作罢,且她心里深处,也不是没想那样的想法。
凤酌,究竟还将她看不看在眼里?
被不待见的人惦念的凤酌,与徒弟不慌不忙的行了四五天,到了第一座的玉矿山,她倒是像模像样的带着楼逆进出玉矿山好几次,还专门解了原石出来与他讲解,旁人看了,自是认为这师徒真是教授的认真。
不过两日后,凤酌带着楼逆继续往北边走,沿途偶有休憩,更多的时候,凤酌专捡深山老林走,偶遇山林畜牲,她便指使徒弟动手打杀,就着林间干柴,就是好一顿美味的烤肉吃。
暮色来临之时,没了村野过夜,凤酌也总能在楼逆惊讶的目光中找着干燥而温暖的山洞宿夜,时日久了,楼逆练就不凡烤肉技艺的同时,对自家师父在山林之中如鱼得水的本事也就见怪不怪了,转瞬,这种钦佩的背后升腾而起的是心疼。
他不晓得凤酌究竟是历经了怎么样的磨难,才有了这样的本领,说是经验老道的猎人都不为过。
在楼逆的这种心疼之中,十日后,凤酌带他出了山林,视野望去,他们竟然出现在座村落之中。
这村落,阡陌交通,菜畦整?,炊烟扶摇,偶见孩童嬉戏玩闹,蓑衣老者含笑垂钓,好生一派世外桃源之景。
“这……”楼逆惊诧不已。
凤酌甚为怀念地望着,她一一种不甚有感情,却意外复杂的嗓音道,“这是桃村,鲜少有外人来此,此地百姓,世代不出村,对外之事,也不甚清楚。”
见楼逆脸上的神色,凤酌继续轻言细语的道,“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,桃村男子,个个生而天生神力,女子则媚骨天成,不过好在,桃村百姓性子淳朴,不惹事端,如此才有这等安宁的日子过活。”
楼逆听闻,他望着凤酌,张了张嘴,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几乎是霎那间,随着凤酌的话,他就已经想到了很多,比如天生神力,这样的勇者若投身沙场军营,足以以一抵百,更可单独训养成一支精锐暗卫,而媚骨天成的女子,用的好,那便有倾城倾国的祸水之势,不费一兵一卒,就可倾覆天下。
然,凤酌最后一句话,轻飘飘的就打消楼逆的所有想法。
他嘴角上翘,眼梢流泻过滟潋的银光,虽还觉得十分可惜,可他也晓得师父的意思,故而道,“真是不易,弟子晓得师父的苦心。”
凤酌点头,这当已有位身穿粗布短襟衣裳的老者携一名总角幼童过来。
凤酌眸色一怔,这老者她上辈子自是认识的,实际当时她是误入此地,并身上带伤,便是此老者悉心照料,才致伤好。尽东低弟。
她略有慌乱地行了一礼,“老人家好。”
那老者银须白发,面有皱纹,慈眉善目,十分亲切,“两位,从何处来?欲到何处去?”
凤酌微微一笑,上一辈子,这老者见她的第一句话,也是这般,她想着便道,“误入而来,去该去之地。”
老者点了点头,他眯眼打量楼逆,半晌摇了摇头,颇为可惜的道,“公子乃人中之龙,只是可惜,可惜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