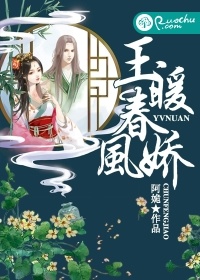凤酌呼出一口浊气,缓缓睁眼,有瞬间的茫然,尔后琉璃浅瞳转了转。渐渐的有了光彩来。
“师父……”有呢喃如蚊呐的嗓音在她耳边轻唤,那股子喷洒的热气叫她很是不适,然而一身都痛,像是锈住了般,哪里都动不得。
她斜眼看过去,就见一下颌都生出了浅胡渣,凤眼通红似兔子的徒弟可怜巴巴地看着她。
习惯地想皱眉,然连着等轻微的动作都牵扯到伤处,遂疼的她龇牙。
“哪里痛了?师父莫动,有什弟子来就是。”谁也不知楼逆心头汹涌而起的失而复得的喜悦是如何的磅礴,他紧紧拉着她完好的右手。近乎贪婪地看着她得面庞。
凤酌轻轻地哼哼两声,伸出舌尖舔了舔干涸的唇尖。
楼逆一下反应过来,赶紧倒了盏温水,他也不是要亲手喂她,反而是自己抿了口,低头脯给她。
当涓涓细流从干到起火的唇瓣间顺喉而下,凤酌都还睁大了眸子,瞪着他。
徒弟怎可这样做?如此羞耻难当的事,实在叫她羞愤欲死。
她压根就不知,在她昏迷的时日里,更为羞耻的事,楼逆都做了,哪里在乎这点嘴对嘴的喂食。
再一口的时候,凤酌就闭了唇,不肯在喝了。
楼逆捻起自个袖子。小心翼翼地给凤酌揩了揩湿润的嘴角,这才望着她道,“师父,弟子都说要给师父置备玉棺来着,日后弟子走哪都背身上。”
可怜才清醒的凤酌叫这话给惊吓的不行,她不过就是这次伤的重些,可也不是毙命的厉害之处。她心里清楚是看着凶险,可只要及时止了血,多半就无碍。
哪知昏迷半月有余,在睁眼,好生生的徒弟怎的就成这副阴阳怪古里古怪的模样了,说点话很是吓人。
她张了张唇,起先被水润了点喉咙不那么涩疼后,才艰难地吐出字音来,“以下犯上!”
楼逆低笑了声,不甚在意凤酌的呵斥。他单手稍稍掩住赤红的眼梢,不让其中掩藏不住的疯狂偏执吓坏了她。
待这样不能为人知的阴暗情绪缓缓沉淀到心底最深处。楼逆这才感觉到疲惫,可他仍旧不敢合眼,只怕再睁眼之时,如今面前已然清醒的人根本就是梦境一场。
他依然倚靠在床沿下的脚踏上,那脚踏如今被下人铺了软褥,不管是坐还是躺,倒还舒服。
“师父,再睡会?弟子守着师父。”他轻手为她掖了掖被角,单手撑头,眼都不眨地看着她。
凤酌抿了抿唇,这一昏迷就是好些时日,眼下叫她再闭眼,却是睡不着的。
楼逆索性就讲了些这半月以来的大大小小的事,诸如他杀了很多蛮夷,如今外面人的看他如看修罗,朱雀营根本没人敢反驳他的话,再如,京中听闻后,有些不好的传言。
他并不瞒她,好的坏的都不顾及。
而在这样轻言细语的讲诉中,楼逆再撑不住,缓缓闭了眼,如很多个晚上一样,就那么趴在床沿睡了过去。
凤酌自是心疼的,她的心也是肉长的,初初睁眼之际,徒弟眼里的恐慌和绝望她看的分明,而向来风华不二的人,如今这样一副面色苍白,还有短胡渣的落拓模样,一看就是根本没心思打理自个。
她缓缓抬起完好的右手,轻轻碰触了他的发,手就那么搭在楼逆脑袋上,昏昏然又闭眼养神。
整个府上的人,明显感觉得到,自荣华县主转危为安后,那等如阎王的端王殿下,恍若一夜春风来,脾性不暴躁了,也不会动不动就要拿剑砍人,更不会不分场合的放杀气,总归恍若隆冬之后的三月初春,甚至还会笑了。
听闻这消息的许拜和御从远等人,明显也是同样松了口气。
不过御从远却是不敢往京中上表,就是楼逆杀了盘刹一事,他也没向往常那边写奏请,至于皇后知晓这事,也是从旁的得到的消息。
如今,他就在端王的眼皮子底下,有那么端王将剑搁他喉咙上的一遭,他是如论如何都不敢私自妄动。状估广号。
别说他怕死,他担心的是惹恼了端王,整个朱雀大营,会落个不好的下场。
毕竟那样视人命如草芥,是真的骨子里凉薄,他可不会顾及手下将士的性命。
如此一等,御从远就又等了十日,这才见半月有余未出门的端王,俊美无双的来刺史府。
人虽清瘦了些,可精神大好,尤其那双凤眼,比之从前还深邃几分,黑漆漆的,一眼望过去,根本不晓得他心里头在想什么。
彼时,御从远与许拜正在对弈,端王踏进来,他的目光同时在两人身上扫过,嘴角就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。
两人起身行礼,见过端王。
楼逆这才摆手道,“今日过来,是劳烦御都督写封奏表上京。”
御从远并不意外,他敛下眉目,还算恭敬的道,“谨遵殿下之令。”
楼逆一手背身后一手搁腰腹,皮笑肉不笑的道,“御都督太过客气,你我二人,可是生死情谊,比之旁的要好上太多。”
御从远隐在袖中的指尖一动,真想直接说,见鬼的生死情谊,谁敢和一修罗有情谊了。
一边的许拜也抽了抽嘴角,他一向就不喜这样的弯弯道道,可眼下,又算是见识了堂堂端王殿下的厚脸皮。
“不知这奏表要如何写,还请殿下指点。”话到这份上,且形势比人强,御从远也就顺势低头,直接问道。
楼逆轻笑了声,他意味深长的看了御从远一眼,心里头就有点慌了,这会已经过去一刻钟,他出门之际凤酌在用粥,也不晓得这会用完没有,是何人伺候的?也不知尽不尽心?
他满脑子都是凤酌,也就没了寒暄的心思,直接道,“直言便可,御都督不会隐瞒。”
御从远一惊,这还没上表,京中就有人晓得楼逆在边漠的所作所为,就他晓得了,早有人在朝堂参本了,眼下,竟还要如实上表。
楼逆没功夫理会御从远,吩咐完毕,他一挥手又如来时般匆匆回去了。
御从远愣了愣,他回头看了看许拜,“端王,走了?”
许拜看了他一眼,懒得回答这等白痴的问题。
御从远好一会才反应过来,他叹息一声,重新坐回棋盘边,皱着眉头,摸着脸上的半张银纹面具,近乎喃喃的道,“他,想干什么?”
许拜可不会想那般多,即便眼下再想的多,在这远离京城的绥阳,从来都是手里又兵的人说话份量重,故而他对御从远的杞人忧天嗤之以鼻,“端王想做的事,是你我之流能阻拦的?若有此心,还不若回做个京官,多的事阴谋诡计让你想。”
被这样一噎,御从远也就放下了,不管怎么说,许拜的话还是说的很对,冒着惹恼端王的危险行事,还是不若安安分分的,那人可是……惹不的,兴许还不如去讨好荣华县主来的有用。
说到凤酌,她在玄十五的伺候后,慢条斯理用完半碗山药红枣粥,才刚擦了擦嘴,楼逆就急忙忙的回来了。
她如今已能起身坐在床榻,只是左边半个身子还不怎么能动的,右手却是无碍的,且一双腿也能行走,不过昏迷太久,身子弱,走也走不了几步。
见凤酌疑惑看着他,楼逆进来,他便挥手让玄十五出去,亲自拿了外衫给凤酌披身上,“弟子不放心,到刺史府吩咐了几句就回来了。”
刺史府距离眼下这宅子还是颇有段距离的,根本不是一刻钟就能来回的事,除非当街纵马。
“弟子当街纵马了。”
果不其然,凤酌才这样想,楼逆就交代了。
凤酌睨了他一眼,这种事她也不好说什么,故而并未有呵斥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被这样一噎,御从远也就放下了,不管怎么说,许拜的话还是说的很对,冒着惹恼端王的危险行事,还是不若安安分分的,那人可是……惹不的,兴许还不如去讨好荣华县主来的有用。
说到凤酌,她在玄十五的伺候后,慢条斯理用完半碗山药红枣粥,才刚擦了擦嘴,楼逆就急忙忙的回来了。
她如今已能起身坐在床榻,只是左边半个身子还不怎么能动的,右手却是无碍的,且一双腿也能行走,不过昏迷太久,身子弱,走也走不了几步。
说到凤酌,她在玄十五的伺候后,慢条斯理用完半碗山药红枣粥,才刚擦了擦嘴,楼逆就急忙忙的回来了。
她如今已能起身坐在床榻,只是左边半个身子还不怎么能动的,右手却是无碍的,且一双腿也能行走,不过昏迷太久,身子弱,走也走不了几步。
见凤酌疑惑看着他,楼逆进来,他便挥手让玄十五出去,亲自拿了外衫给凤酌披身上,“弟子不放心,到刺史府吩咐了几句就回来了。”
刺史府距离眼下这宅子还是颇有段距离的,根本不是一刻钟就能来回的事,除非当街纵马。
“弟子当街纵马了。”
果不其然,凤酌才这样想,楼逆就交代了。
凤酌睨了他一眼,这种事她也不好说什么,故而并未有呵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