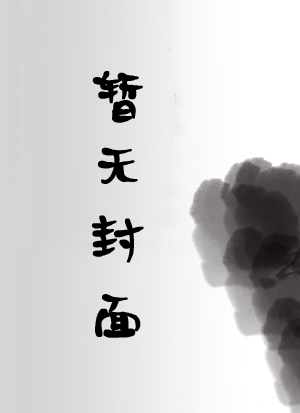其后的日子里,邹顺旁敲侧击,了解了王洁的信息。
姓名:王洁,性别:女,民族:汉,祖籍:四川省旭宁县,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。其父母早年出去打工,在外地生下了她,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,据说姐姐和她极其神似也极其形似,但只是据说,因为邹顺从来没见过她姐姐。
由于某些无法述说的原因,一家人在今年全部归来,父母种地来供养三个孩子读书,而王洁和她弟弟自然就入了石田小学。有趣的是,按照辈分,王洁竟然还是王笑笑的小姑,当邹顺听到这个消息时,不禁一笑,按照辈分,自己还是王笑笑的舅舅呢!
有了王笑笑这层关系,邹顺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,又悄无声息地通过这层关系打听了许多关于她的信息,王笑笑也乐得讲述,体现自己的价值,两人各得其乐。
自从邹顺迷恋上王洁之后,每天就想着如何制造机会和她见面。一下课,就拉着箫鹏去上厕所,但醉翁之意不在酒,四年级的窗子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吸引着他往那里看去,即使迎面走来了人也毫不退让。
只要一走近那扇窗子,他只感觉心脏呼之欲出,呼吸难以为继。王洁性格内向,不喜动,好静,下课一般都待在教室里。邹顺的眼神总是似有似无地穿过窗子,飘过她的短发,掠过她的耳根,停留在她的侧脸,那精致的侧脸往往让邹顺呼吸骤停,直到最后邹顺再看不到她的身影,才依旧拿出自己高年级的风范,抬头挺胸,泰然自若,只是在前一秒,他的却卑微到了尘埃里。
王洁也不是孤僻之人,她也会和同学一起玩跳皮筋,也会玩单脚跳和跳房子。当她跳皮筋时,邹顺也乐得在一旁观看,因为学校人比较少,所以几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玩也是常事,其中自然也会有六年级的女同学,而邹顺则会打着看班上女同学的幌子,在一旁或蹲或站,默默观看,有时也和她们搭搭话,虽然其中也有人邀请他一起玩,但邹顺还是忍痛拒绝,倒不是说他跳皮筋技术差,虽说比不上很多女生,但是由于他的弹跳很好,所以跳皮筋也不会吃太多亏。
他之所以拒绝,或许是那怯懦的自卑感在翻腾,看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就在眼前,连话都不敢和她说,又哪有勇气和她一起玩耍?那可鄙的自卑啊,不知抹灭了多少光明!很多事情明明只要伸出手,便可轻而易举做到,可是那自卑如同幽灵一般,缠绕,束缚,囚禁,吞蚀着邹顺,使他无法呼吸,无法动弹,无法呼喊,无法追逐光明。
或许这也怪不上邹顺,每个男孩子生命中必然会有一个女孩,她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虏他的心,把玩他的心,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,即使他平时挥斥方遒、指点江山,受尽尊崇,却唯独对她无计可施,或许这便是妺喜、妲己、褒姒的故事得以流传的原因。
上天在爱情这一点上还是比较公平的,不管是朝堂之上定人生死的帝王,还是军营之中运筹帷幄的将帅,也不管是街里坊间清污脏除秽的工人,还是府邸之下惟命是从的仆人,在爱情这件事上都是平等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劫数,都有自己的命运,谁都无法幸免。只是来的时间早晚罢了,如果还没遇到那个人,不要心慌,也不用着急,因为这个人的到来并不一定是件好事。
时光如水,邹顺的日子就在每天的窥视中悄然流逝,一转眼十月将至,十月份,是一个值得所有学生欢呼的月份,因为这里有想想就足够兴奋的十一长假,这对刚开学一月的学生来说自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但邹顺的兴奋却不在此,国庆,学校会有一个文艺汇演,到时会有很多家长前来观看,而主持人名单业已公布,王洁是新转来的优秀学生,学校一般会照顾一下,在各个方面提供机会,所以王洁被选做主持人倒没什么疑问。
而另一个主持人——邹顺,虽然在班上一直都是尖子生,但似乎没什么主持的天赋,但在那个年代,一个学生只要成绩够好,学校就会认为他其他方面也好。
在那样的穷乡僻壤,一个个家庭都还在为生存和发展奔波,哪里顾得上其他的诸如主持之类的技能训练,所以,既然大家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,那么只得再次应用那个万能的标准——成绩,只有成绩才能说话。
说到成绩,邹顺在上学期做了一件刷新学生们认知的事,那时,他还在读五年级,小升初统一考试,有比他高一年级的两兄妹,或许是因为家里要带他们出去读书,所以他们没有考试,直接挥了挥衣袖,只留下一脸黑线的校长,因为他们已经报名毕业统考,所以就空了两个名额,这两个名额空着自然不好,当然,怎么个不好法,邹顺是无法说明白的。
只是有一天,校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,简单对他说了这件事,最后邹顺被通知,去顶替那对兄妹中的哥哥参加考试,而妹妹的名额,校长去镇上中心校又找了一个学生,这个学生也是邹顺的熟人,因为他们也曾同过窗,既是好友,也是对手。
在正式参加考试之前,邹顺和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一次摸底考试,在那次考试中,邹顺拿了全班第五,本来颇有声名的他因为这事达到了他声望的顶峰。
六年级的学生他大多认识,有的还很熟,关于考试这件事,多年以后都还偶尔被人提起。邹顺在这次考试中,只记得一个细节,在那份试卷中,有一题是填写诗词,其中一句是“瑞雪兆丰年”。考下来,六年级的班主任就火了,因为连五年级学生都知道的谚语,而他们却不知道。他们只得说没学过,确实,他们没说谎,那句谚语确实没学过,因为那是邹顺从老版的教材上看来的。
邹顺受到这件事鼓励很大,于是他回家翻起了哥哥的老版数学教材。爱因斯坦说:教育就是当你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。既然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大都要忘,为何还要学?或许是因为现在的学习不再是学习刻板的教材知识,更多的是学习方法和学习思维吧。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说:在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,能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,不再是你掌握了多少知识,而是你的学习能力,只要拥有学习能力,就能原地逆袭。
而邹顺无疑是拥有学习能力的,他花了一天时间,就把六年级的数学教材吃了个七七八八,虽然和学懂还有很大差距,但要应付考试应该还是绰绰有余了。最后考下来也和邹顺预料的差不多。多年以后,当邹顺想起这件事,依旧会沾沾自喜。
邹顺就这么和王洁组成了搭档,一起主持国庆节目。当邹顺被叫到办公室,听说王洁要和他搭档时,只是觉得难以置信。虽然他这个主持人的位置并不能让他和王洁的关系有什么改变,但只要一想到自己将和王洁一起登台,一起合照,他的心脏就急速跳动,似要破体而出。
邹顺其实很是郁闷,一般的活动都需要反复排练,直到累了方才罢休。可是关于主持人,老师却几乎不主持排练,只叫他们回家好好熟悉台词,到时对一下台词就好。邹顺心里满是不情愿,但又无计可施,只得安慰自己:虽然不能和她天天排练,但只要能和她同台,便已是美事一桩!
想想还真是讽刺,邹顺和王洁已经是搭档了,可是他们还没好好说过话,基本属于零交流的状态,或许他真应该好好改变一下了。
邹顺回家在他的日记本里这样写道:“我该怎样描述我心中的激动?感觉上天给了我一个莫大的机会,每个人都是那么可亲可爱,我将要和王洁一同登台,一同主持节目,我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?感觉一切文字都失去了它们的色彩……”
六年级学生稚嫩的文字在笔记本里流洒出来,同时流泻出来的还有他炽热的情感。
为了使自己表现更出色,邹顺只能在私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主持稿,以前那么多次国庆演出,邹顺每次听到主持人的那些稿子都觉得枯燥无比,可是今年,邹顺看到主持稿,却只觉得无比亲切。每次细细读着稿子,一边读一边想着心上的人儿,想着她柔美的嗓音,想着和她一起登台的场景,不觉太阳就已落到了西头……
虽然邹顺准备得无比充分,可是国庆节却在他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翻了过去,什么都没留下,甚至连记忆都像是被人抹掉了一般。邹顺和王洁虽然搭档完成了一次主持,可他们说过话吗?邹顺不知道,或许他们打过招呼吧!
在课间,经常看到她和同学玩跳房子,邹顺的双脚总会不由自主地往她所在的方向慢慢移动。看见她们玩得这么开心,邹顺感觉有几个字像要蹦出自己的嘴,可是看到王洁窈窕的身影,那简简单单的“加我一个吧”就只能堵在喉咙里。有时候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争执过度,邹顺就会胸闷气短,虚汗直冒,直到他远远地逃离战场。
其实邹顺玩跳房子是有一手的,或者说他作弊可有一手了,每次他背对着扔瓦片的时候总能扔到好位置,因为他在扔的时候总能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往后一瞥,对他来说,这简简单单的一瞥就足够让他把握好力度,然后将瓦片扔到自己想要它去的地方。
虽说农村孩子运动细胞普遍比较强,但在平衡等方面却很差,但邹顺能兼而有之,协调发展,这也就垫定了他在跳房子这一事业上稳定发展的基础。
一个干冷枯燥的日子,此时虽是十二月。而且此处又是山村,山多,海拔也高,但由于石田村纬度在三十度左右,到了十二月依旧没有下雪的迹象,在邹顺的记忆里,下雪这事得等到一月才行,虽说有时在十二月便已经有了下雪的迹象,但真正要看雪还是要等到一月。
这一天虽然干冷枯燥,但在黄历上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日子,适宜做的事情有很多,但邹顺只记得宜入宅,为何?因为今天是村里侯子才乔迁的日子,其实侯子才在村里口碑并不好,但在这三村五寨,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,若是别人有了红白喜事不去露个面,说出来对名声也不太好,所以,除了那些真正和他有过不去的坎的人除外,村里人基本都会来捧个场。
孩子们尤其喜欢这种事情,有九大碗可以吃,有牌场可以看,还可以参观人家的房子——即使自己家里破败不堪。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和一群伙伴疯玩,有时主人家有丧事,一家人都在痛哭流涕,但却依旧无法影响孩子们的笑语欢颜,有时主人家在灵前磕头、流泪,而另一边就可能有孩子在偷笑。当然,这只能说是童行无忌,毕竟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特权。不过,侯子才是乔迁之喜,自然不会有此等画面出现。
此等日子,王洁肯定也是到了的,那天虽然很冷,邹顺的心里却无比温暖。
无穷的创造力,健壮的身体,活泼好动的性格,是那个年纪的孩子的共性。因为在冬天,晚饭摆得早,大概四点钟便已结束,而一群孩子,吃完饭,便肯定要思考玩乐的问题。有人提议玩金盘银盘,所谓的金盘银盘,就是把人分成两方,一方负责跑,一方负责抓,就和警察抓小偷差不多,跑的人有大本营,被抓的人会被送进监狱,当然,可以去营救。这个游戏需要很好的团队协作能力、斗智斗勇能力以及长途奔袭的能力,有时候已经抓住了一大半,却一下子被对方全救走了,对心态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这个游戏是男孩子的最爱,也是邹顺的强项,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,那就是不适合男女生一起玩,因为这娱乐项目可以说有点野蛮,有时为了救人横冲直撞,撞到人在所难免。
今天有很多女生,这游戏便不得不否决。最终还是决定玩单脚跳,这个游戏比较适合男女生一起玩,大家划定一个区域,根据石头剪子布或者重九九等方式选出一个用单脚跳着去抓人的人,而其他人就负责跑,由于区域比较小,抓人者只需把被抓者赶到一个狭小的角落,抓人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,但是如果遇到那种身体非常灵巧之人,或许抓不到他,还反倒被他戏弄也未可知。这个游戏男女皆可,自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
首先大家通过重九九来决定谁去抓人,所谓重九九,其实就是参与者伸出右手,四指紧握,拇指伸出,重在一起,从下往上数,第九个即为“幸运儿”,若是不满九人,则循环计数。这样的决定方式有一个坏处,那就是只要你的计算能力、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足够好,你就可以在一瞬间推算出谁是“幸运儿”。
谈话之间,箫鹏已经伸出了右手,王洁紧跟其后,后面的人纷纷跟上,邹顺最后伸出手,只是他把自己的手放在了最下面,也就是箫鹏的下面,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往上面放,最后一数,“幸运儿”是箫鹏。
只听箫鹏抱怨了一句:“不至于这么倒霉吧,竟然来个‘开门红’。”邹顺脸一红,急忙打圆场,“反正你跳的快,抓到人也就是一会的问题嘛。”箫鹏笑了笑,没说话。
游戏正式开始。邹顺看着场中跳跃的箫鹏,心里很不是滋味,感觉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兄弟。不过也就一会功夫,他便从其中脱离了出来,而把目光转向了王洁,看着她在场内左躲右闪,邹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但每次她都堪堪避过,邹顺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。
王洁那一头干净简洁的短发在眼前晃来晃去,邹顺的心也随之晃来晃去,如风摆杨柳一般,飘飘忽忽,不知所适。
天随着他们脚步的跳动,蒙上了一层黑纱,而场中人却浑然不觉。等到他们发现,远方人家已经点上了零星灯火,已经来临,邹顺不禁抱怨,但抱怨归抱怨,上天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有所改变,该来的始终会来。
天黑了。
大家停了下来,商量接下来玩什么,去哪玩,只听王洁说道:“要不我们去邹顺家玩吧?”
邹顺浑身一颤,有如雷击,脑中一片空白,无法思考,更无法回答,震惊、狂喜、害怕、一股脑全涌了出来。然而邹顺呆立的时间太长,见他没有言语,大家还以为他有什么不方便,另一个女孩子打圆场说:“那样不太好吧,都已经晚上了,我们还是去侯子才家逛一圈,然后各自回家吧。”这女孩平时和王洁很是玩得来,因此对王洁很有影响。
邹顺刚反应过来,却只听王洁说道:“这样也好,我爸爸也叫我早点回家。”邹顺一听这话,顿知无法挽留,只得罢手。在一群人浩浩荡荡向侯子才家开路的时候,邹顺却推说自己有事必须先回家,大家也不强求,只得由他去。
邹顺并不是不想和大家一起去,只是现在他的心中有一口气,满满地堵在胸口,像沉睡千年的火山一般,沉睡千年,积蓄千年,只为喷发的一刻。邹顺心里的那口气,如果不完全发泄出来,他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
邹顺看着众人走远,转身,撒开步子,向着远方的山峰奔去,每跑几步,他就低吼一声,风扑打在身上,有点刺骨,但他丝毫无感,他一直在逼问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发呆?为什么要发呆!越想越气,吼声也越来越大。
虽然天黑,但借着一点朦胧夜色,以及在这山旮旯里摸爬十多年的经验,半个小时后,他来到了一处山顶,手臂青筋暴起,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把心中的愤怒全部宣泄了出来,吼声从喉咙里迸射出,却一点一点地被这无边的黑暗吞噬,最后连骨头渣子也不剩,全被这无形的黑暗、罪恶的黑暗吸收了。
回家的路上邹顺轻松了许多,好像刚才在山上怒号的另有其人一样。猛然间,邹顺发现远方路口处隐隐绰绰似有人影,但仔细看又似是幻觉。邹顺心里一紧,心想这大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来这种地方,难不成是……邹顺越想越怕,赶忙加快步伐向家里奔去。
越接近路口,邹顺的心揪得越紧,脚上的步子也迈得越快,越大,一心向家。
路口处有一株树,乃是百年乔木,一年四季浓密如一,不因天时地势而异。树存百年,历百年风霜,经百载雨雪,年轮所记,皆为历史。见证了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兴衰成败,如今已轮到邹顺这代人。
若在平时,邹顺是很喜欢这棵树的,树下也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可是现在,晚上七八点,阵阵阴风吹来,树枝随之起舞,远远看去阴森诡异,邹顺不由得再次加快步伐,他一秒都不想待在那里。
当邹顺将要掠过那百年乔木之时,一阵笑声传来,虽然这笑声并没有恐吓的成分,但邹顺还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。当他思考着自己能否跑得再快一点时,身后却没有了笑声,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话:“阿顺,你就这么胆小吗?”这声音极是亲切,邹顺对这声音的主人也极为熟悉,他慢慢停下来,转过头,只看见箫鹏慢悠悠地从树后走了出来,向着邹顺的方向迈动了步子。
“看你在远处就已经开始害怕,我都没有扮鬼来吓你呢,没想到你还是被吓成这个样子”箫鹏一边走一边笑着说。
邹顺知道狡辩没有用,便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道:“有本事我们互换情景,看你怕不怕!”
“哦?互换情景,那是不是连喜欢的人也要互换呀?可是我并不喜欢王洁那个姑娘哎。”箫鹏的语气满是玩味。
邹顺一听这话,瞳孔猛然一缩,两只眼紧紧盯着箫鹏——这个和他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玩伴。而箫鹏的目光则平静如水,没有一丝波纹,坦然而又自信地望着邹顺。虽然夜很黑,但两个孩子在这山旮旯都摸爬滚打了十来年,这黑夜自是不能对他们有所阻碍。两个发小的关系在这一瞬间变得极其微妙,稍不注意便会爆发一场战争。也不知过了多少光景,不知又有多少生命在他们对视的光景里悄无声息地逝去,在世间万物依旧运作的这段时间里,他们就这么静静对视。
最后,邹顺败下阵来。
邹顺自嘲地笑了下,“我知道瞒不过你,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。是因为今天的事吗?”
“今天的事充其量只能说是证明了我的猜测,更多的是平时的表现吧。自从她来到这里,你难道没发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吗?”箫鹏有些激动。
“或许吧。”邹顺含糊其辞。
“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”箫鹏看出了他的敷衍,直接问道。
“我也不知道,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”邹顺的双眼开始变得迷惘。
“我想告诉你的是,你比她高两个年级,而且你马上就要去初中了,我们都还小,有些事把它珍藏在心中就好了。王洁是很优秀,但如果你把她当成妹妹或者挚友来看的话,你会过得比现在开心。”箫鹏故作老成。
“有些事情说起来总是比做起来简单,你知道的。”邹顺有些不悦,作为自己的兄弟,他不鼓励自己倒也罢了,反倒劝自己放弃。
“不管怎样,我都尊重你的选择,并且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,只要你需要我。”箫鹏一字一顿地说完。
邹顺看着他坚定的神色,不发一言,两人就这么看着对方,过了许久,邹顺露出了一丝笑意,他似乎又看见了每次打架时都护着自己的箫鹏,每次有好东西都会和自己分享的箫鹏。
当晚邹顺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一句话:“我实在难以想清楚男孩子为什么喜欢女孩子,为爱吗,为性吗,抑或是自然本能?”多年以后邹顺又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句话:“若不是因为性欲,其实大部分男孩子更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耍。”
自从上了六年级,邹顺每天都会写日记,倒不是为了所谓的提高写作能力,而是为了记录生活中发生的点滴,以便自己在将来再次翻阅时可以回想起如今发生的种种,事实上,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,多年之后邹顺再次看到自己的日记时,一边哂笑当年稚嫩的文笔,同时却又深深地为之动容。虽然其间的很多场景都已模糊,可是那些模糊的画面却依旧深深拨动着他的心弦。
自从那夜之后,邹顺知道,自己对王洁的感情已经完全暴露在了箫鹏眼前,不过这并无大碍,反正箫鹏是自己最好的兄弟。甚至,邹顺还庆幸箫鹏知道了这件事,因为他还能给自己提供一些建议,以前邹顺畏首畏尾不敢做的事,现在有了箫鹏的鼓励,或者说叫怂恿,也开始有了尝试。
时光一如邹顺门前溪流,静默地流了过去,并未激起一丝浪花,邹顺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去上厕所,顺便偷瞄一眼四年级教室的窗子,偷偷看一眼心上的人儿。
一次,邹顺又像往常一样挟持箫鹏去厕所,在经过那扇窗子时,发现他朝思暮想的人儿正在低头看着什么,就在邹顺准备趁她不注意多看一眼时,她像是觉察出了什么,猛然抬起头来,看到邹顺和箫鹏,惊愕了半秒钟,但惊愕之后,她向着他们的方向,笑了,邹顺就这么看着一朵雪莲在她的脸上绽放,那一刻,邹顺原本已千疮百孔的防线顿时灰飞烟灭,他只愿时间能够在此时停止,只愿自己能看着她脸上的雪莲死去,死后融进她一尘不染的眸子里。
转眼已是六月,遥远的火球不凉不热,就像是早晨八九点,虽然太阳普照,甚是耀眼,却又无甚热气。
这是小学的最后一程,林海音女士的《爸爸的花儿落了》,邹顺他们已然学过很长一段时间了,但文中出现的《骊歌》却在邹顺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: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问君此去几时来,来时莫徘徊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,唯有别离多。
剩下的日子不足一月,自己将和身边这些可爱的人儿永远地离开这所学校,离开这座乐园,去接受无法预测的中学生活。若仅是如此,倒也罢了,但对邹顺来说,还有更为悲痛之事,那便是将要离开王洁。日后山长水远,再难见到自己心心恋恋的女孩,每每念之,无不心如刀绞,如坠冰窖。
但该来的始终会来,六月二十号,他们结束了考试,突然之间,他们就像被学校抛弃的孩子,无所适从,心里空荡荡的,茫然无措,平时上课一心想着放学,可是现在可以真正回家却又觉得学校竟是那么可爱。
邹顺和箫鹏步到学校门口,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,转过身来,目光慢慢地移过校园里的一草一木,高大的沙树早已被砍了头,剃了枝丫,看去甚是孤零。花坛里的花草,全是他们从自己家里移栽过来的,那个时候为了建设校园,这群孩子可没少花力气,当时邹顺扛着比自己还长的锄头在校门外铺路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只是转眼已是两三年的时光,如今他们就这样被“赶出”了这座校园。
邹顺长叹了一口气,先掉过了头。